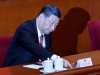我父亲给我母亲拍的第一张照片,在藏干校门口,她15岁。
1、
这次,我从1957年说起吧。那年,因为阿佳(姐姐)不愿接受母亲安排的婚姻,我就跟着她从后藏家乡来到了拉萨,理由是朝佛,其实是逃婚。不久有了一个很偶然的机会,但实际上是命运的安排,故事很长,以后再给你讲。总之我和姐姐进了藏干校,也就是共产党培养藏族干部的学校(注:之前是西藏军区于1952年创办的西藏军区藏文藏语训练班、西藏军区干部学校,1956年改为西藏地方干部学校,后来又改为西藏行政干部学校、西藏师范学校、西藏师范学院,1985年更名并扩充为西藏大学),当时我14岁,用现在的话说,从此参加了革命。
藏干校就在以前树木很多的仲吉林卡那里,夏天时贵族俗官们爱在仲吉林卡游玩。拉萨人称藏干校是“大洋洛乍”(大洋学校),讽刺藏干校的师生都是冲着大洋(即银元)去的,因为每个月共产党都要给我们发大洋。除了吃穿住包干,起先每个月发四十八块大洋,不过愈来愈少,到了1958年年底,每个月只有八块大洋。我和姐姐领到四十八块大洋的日子可能有半年。不过我的大洋都放在姐姐那里,说是替我保管,但交给我用的很少。

我父亲在藏干校门口的留影,他21岁。(唯色提供)
藏干校有七个大班,每个大班下面四个小班,每个班二三十人吧。是按藏文程度来分班的,一班文化程度最高。记得进藏干校的时候考试,让我们念报纸,让我们写藏文,然后姐姐在一班的二班,我在一班的四班。二班至七班的学生都是解放军进藏路上修路、修房子找的民工叫“阿波”。藏干校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底层藏人,出身成分高的很少。我被同学们叫做“色姆古修”(小姐),或者“哦玉珍啦”,“哦”是敬语。还有一些商人的子女。后来,藏干校的学生除了在公检法单位的比较多,有的进了军区总医院当护士,有的是其他单位比如粮食局的干部。还有人是售货员、居民。
在藏干校,藏人学生基本上不会说汉语,男女生差不多各占一半。汉人学生都是金珠玛米(解放军),是来学藏语的,可能也有别的目的吧,比如找对象。解放军大概有两百人,“藏语文学习队”,大多数是汉人,只有十几个藏人几乎都是康区来的,有巴塘的、甘孜的、德格的,像你父亲。他们全都分散在我们这些班里,当插班生。

穿军装的我父亲与同学们的合影,右二是我母亲。(唯色提供)
我们的课程有藏文、数学、政治。后来教过一点汉语拼音。我们班主任是汉人,叫孙主任。副班主任是巴塘女人,叫卓嘎。政治老师叫阿旺平措,就是朱家训,后来才知道是你父亲的德格老乡,两家关系很深。我们班上教藏文的老师是个贵族,“仓郭”,意思是头发盘起来,里面有金嘎乌顶在头上,象征地位高。他教过《萨迦格言》、《诗歌文法》。给藏文好的班上课的老师还有噶厦政府的孜仲(僧官)。
藏干校最重要的课程是政治。主要学习“十七条协议”(注:即1951年中共政府与西藏噶厦政府签订的《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》),其他学了什么不记得了,就记得学了“十七条”。体育课教广播体操。每个班还有表演歌舞的宣传队。喜欢跳巴塘弦子。我们班的巴塘弦子还是你父亲教的。那时候巴塘人很有名,应该跟平汪先生(注:即平措汪杰,巴塘人,西藏最早的共产党人,作为率先同中共军队一起入藏的藏人,在1950年代是中共体制内地位最高的藏人)有关系,他带来了很多年轻的巴塘人。有一次“五四青年节”,我们去了布达拉宫前的修赤林卡(注:属于达赖喇嘛的法座园林)跳舞。你父亲他们“藏语文队”的节目是合唱“九九艳阳天”(注:1957年红色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插曲,关于军人与村姑的爱情),你父亲拉手风琴。“五一”、“七一”、“八一”、“十一”我们都要唱歌跳舞。

1958年“五四青年节”,藏干校学生在布达拉宫前歌舞,右二是我母亲。(唯色提供)
最难忘的是劳动课。就是种菜。过去是仲吉林卡的草地,被我们开垦成了大片菜地。主要种莲花白、萝卜、土豆这“三大名菜”。种的这些菜还选送去北京展览,因为长得特别大。我们还去拉萨的很多厕所掏粪。这是我最烦恼的,我哭哭啼啼地对姐姐说:在家从不干活,却在这里掏粪,阿妈啦说过我们不听她的话,会干佣人的活,现在她的话应验了。我让姐姐带我回家,但姐姐不肯,还训斥了我,我也没办法。

穿便装的我父亲挎着他心爱的相机(唯色提供)
没过多久你父亲出现了。我们正在上课,他和另一个德格人多吉平措,穿着军装进了课堂。他那时候头发长,还烫得卷卷的。衣服也多,军装、藏装、西装、便装换着穿。当时我们同学都叫他“玛本灼灼”,意思是爱打扮的军官。爱穿又黑又亮的马靴我现在还留着。我觉得这个人好奇怪呀,上午穿的是军装,下午穿的是西装,过两天又穿的是藏装,还常常请假不上课。后来才知道他是军区联络部的军官,因为工作需要,经常跟上层贵族打交道,和他们一起打麻将、跳交谊舞,所以要化装。
你父亲那时候就很喜欢拍照。他有一架相机,是他用在边境待了两年的薪水,在帕廓的店里买的,还是德国的蔡司相机,很漂亮。他用那个相机给我拍过很多照片,也用那个相机在文革时拍了很多照片。他给我拍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在藏干校门口拍的,我很害羞,两只手都不知道怎么放。你看照片上,我戴着我的爸啦在帕廓的店里给我买的罗马手表和翡翠手镯,还有两枚心形状的金戒指,但后来除了一枚金戒指,因为送给你父亲,所以一直留存到现在,其他宝贝,我去北京上学时交给姐姐保管,但最后都成了她的了。

我父亲在我母亲演出前拍下她的美(唯色提供)
至于我跟你父亲恋爱的故事很曲折,这里不说了,以后再讲。总之因为我的家庭成分是“领主代理人”(注:中共给西藏人口划的阶级成分,包括“三大领主”即官家、贵族、寺院和上层僧侣及其代理人组成的农奴主阶级,以及农牧奴),影响了他的入党和升职,八年恋爱期间我们还不得不分手过,但他舍弃不下这份感情,又专门跑到政法干校来找我,这样我们又和好了。现在回忆起来,我在藏干校两年,认识了你父亲是我这一生中最幸福的缘分。如果我不去藏干校,就不会认识他,也就不会有你了。